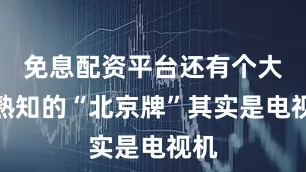自黄桥战役落幕,两党间的摩擦与反摩擦愈发激化,局势愈发紧张。彼时,皖南新四军近万兵力正遭受国民党重兵的严密监控,而苏北韩德勤部数万士兵则被八路军新四军所环绕。此情此景,宛如我方之子落入你手,而你之子亦在我掌握之中,彼此皆怀有戒心,从而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然而,在1940年11月26日,中原局毅然发起了曹甸战役,此举打破了僵持的局面,进而成为引发皖南事变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一、拖、拖、拖
新四军军部孤悬于皖南,中央对此早已作出明确指示。1940年伊始,即1月、3月与4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在延安多次通过电报催促项英,要求其迅速将新四军军部北迁至苏南或江北地区。及至5月,已驻扎苏南的陈毅、粟裕亦向项英发去电报,建议鉴于“国民党亦希望我方退出皖南”,我方应当“以退为进”,将军部及皖南主力东迁至苏南,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故。
面对中央的指令以及江北陈粟等人的提醒,项英的态度显得消极,甚至有所抵触。他坚信:“在战略布局上,北方必须得到南方的协同支持”,“皖南在所有情形下,都必须坚持独立行动,坚定不移地维护南方的立场。”
4月3日,毛泽东等人鉴于“顽方或许会凭借其兵力优势对新四军军部区域发起攻击”的担忧,向项英咨询:“若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袭击,我们是否有突破重围、减少损失的应对策略?是采取向南进行游击战更为合适,还是向东与陈毅部会合更为有利?是否已经完全无法实现渡江向北的战略?”
接到主席的电报后,项英回应道:“横渡长江,实属不易,敌方在长江的封锁愈发严密,江北的桂军已在江边布下重兵。”“若向东进发,我方已有安排,但需突破两道封锁线,经历数场激战,方能与陈支队汇合。至于苏南地区,形势并不乐观……”
他的意图清晰明了,一遍又一遍地阐述诸多理由,分明是因不愿告别皖南。
10月9日,恰逢黄桥战役即将落幕之际,刘少奇再次向项英发去电报,强调:“鉴于皖南设立军部已属不切实际,我建议迅速将部队北迁。考虑到目前交通尚属畅通,若稍有拖延,恐遭顽固势力截断封锁,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项英并未采纳这些意见。11日,他在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及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表示:“综合考虑各方形势与现有条件,鉴于军部北移的困难以及三支区域(面积狭小,敌友双方均难以立足)的不便,我们认为以军部现址作为战略基点更为适宜。”
在接到项英拒绝搬迁的电报之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并以毛、朱、王三人的名义再次向项英发出指示:“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域,我方不宜开展任何形式的游击战,曾生部队在东江的失利便是显赫的例证。因此,军部应抓紧时机迅速渡江,以皖东地区作为我们的根据地,务必不可拖延。”
“为确保未来我能实现更广阔的发展,坚守皖南阵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此刻放弃,日后将难以再次掌握这一坚实的支撑点。”他还强调,“为确保皖南阵地的坚守,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兵力作为保障,因此,原有力量的北移不宜削弱。”
这已非单纯的建议或意见,而是对中央指示的公然违抗。
曹甸战役结束之后,皖南我军顿时陷入了极其险峻的境地,这一点即便是对战争一知半解的孩童也能轻易看穿。然而,似乎项英却未能洞悉此情势。尽管延安的毛泽东、重庆的周恩来、中原的刘少奇以及苏北的陈毅等人急如星火般地发来催促的电报,他却屡次寻找借口,拖延不决,只落得一个“拖”字。
为了报复我在苏北对韩德勤的进攻,皖南的国民党军队迅速收紧了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圈。然而,必须承认,国民党军的这一合围行动速度极慢,显得颇为迟缓。然而,项英似乎有意与国民党军展开一场速度竞赛,对北移的安排,他总是找借口拖延,一拖再拖。
在重庆,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中,双方约定皖南新四军最迟应在12月31日前向北迁移。然而,进入12月下旬,皖南新四军却迟迟未见行动。26日,毛泽东忍无可忍,以极其严厉的措辞向项英、周恩来、袁国平发出电报:“中央早在一年前便已明确方针,要求你们向北发展,深入敌后,但你们却屡次找借口,拒不执行。”“在全国范围内,从未有过如此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缺乏决断力的军队。”“你们究竟主张何为?是主张拖延还是主张撤退?如此缺乏明确立场和方向,将来必会遭受重大损失。”
即便面对如此严苛的催促,项英依旧执意拖延至两党规定的最终期限——12月底之后。直至1941年1月4日,方才启动了行动。
切勿轻视这短短的四日,1月4日的离去与12月31日之前的选择截然不同。超出了两党既定的时间限制,这让我在政治上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同时,国民党军已基本完成了对战略要地的合围,对我军事上的形势造成了极大的不利。不论从哪个角度审视,我似乎都已先失一筹。李一氓事后不禁感慨:“若能提前四五天行动,恐怕结局不会如此凄惨。”

二、错误的路线
错失了转移的最佳时机,而选择的转移路径更是令人费解。数月前,参谋处便已为北撤行动规划了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自马头镇出发,途经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最终抵达竹箦桥及水西地区,随后沿苏南北渡;第二条路线则选择在铜陵与繁昌之间渡过长江。
第一条路线,即皖南军部通往苏南我军的交通要道,沿线分布着兵站,每座兵站均配备了民运工作组,并设有地方党组织,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此外,这条路线亦系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以及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所共同推荐的。同时,它也是与三战区经过多次协商后确定的最佳路径。
这条与三战区共同确定的行进路径,意味着一旦遇到敌军的顽强抵抗,对方在政治上的处境将变得不利,而我的胜利机会则大大增加。
第二条路线的优势在于其便捷的行程,部队自云岭启程,仅需一日即可抵达铜、繁地域,翌日便能顺利渡江。若采取急行军,甚至可于当夜渡过江河。此外,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所率工作组早在一个月前便已先行,完成了详尽的侦察与动员工作,控制了十二处渡口,并征调了超过两百艘渡船,一次航行便能确保7500人的顺利过江。此外,该路线沿途均由我游击队严密掌控,当时日伪顽敌驻军数量甚少。尽管近期顽军有所增加,但仍有间隙可利用。这条路线正是蒋介石最终确定的行军路线。
固然,这两条路径均面临敌情,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尤其是进入12月底,这些不利因素愈发显著。然而,在权衡利弊之后,这两条路径依旧被认定为最优选择。因此,叶挺坚决主张采取东线,次之北线,并已责令参谋部门针对这两条方案制定出详尽的行动计划,绘制出行军路线图,只待项英最终定夺,即可付诸实施。
然而,正当部队即将北撤之际,项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叶挺关于向东线或北线进发的建议,转而选择了经过章家渡、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天目山、溧阳的南线行进路线。
这无疑意味着,在叶挺将军的亲自督率下,参谋处投入数月辛勤努力所完成的各项准备工作,悉数付诸东流。
项英此番决策,令众人瞠目结舌。选择此路径,不仅路途遥远,迂回曲折,耗费时间过长,且难以确保保密与隐秘。我军孤军深入,极易陷入敌军包围之中。一旦遭遇敌情,身处敌后深远之地,前无村落,后无市集,必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毕竟,事先未曾料到首长会选择此路线,因此对地形缺乏周密侦察,沿途亦未做任何准备。兵站设施匮乏,地方党组织也未开展相关工作,群众基础薄弱,参谋处甚至连此路线的地图都未准备齐全。
选择南线,不仅军事上对我方不利,政治层面亦然。向南行进,步入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其间的行动对民众解释起来尤为棘手。数月之前,那些受国民党操控的媒体便不断炮制舆论,散播关于新四军即将南逃、袭击国军、夺取徽州军火库、推行所谓“三山计划”(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黄山、天目山、四明山建立红色根据地的计划)等谣言。若我方选择向天目山进发,无疑是将把柄拱手相让于顽固派,为他们对我方实施“制裁”提供了借口。
在皖南,新四军中项英素以言出必行著称。在他的固执己见和一意孤行之下,九千余人的新四军军部被迫踏上了这条充满危机的道路。
“甲、我军胜利的关键因素:首先,战略部署精准,使得匪军主动步入我们的陷阱。
……
乙、匪军败亡之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离开老巢,向南越过章家渡,却不幸落入了我国部署下的最严密包围圈之中。
新四军选择此条路径,实为主动投身险境,任人吞噬,此举令敌军意料之外,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力排众议,毅然决然踏上这条本不应选择的道路,进而精确无误地将部队引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若要夸张一点,我竟不禁疑惑,这位副军长究竟是在为谁效力?

三、复杂战术操作
北迁路径已然谬误,在战术层面上,项英亦持续压制合理的观点,导致一误再误。
咋个错呢?
初时,我们在密林中逗留了一整天,耐心等待敌军合围之势的形成。
古语有云:“兵贵神速。”他们本应朝着国民党军的防御区域快速前进,毕竟那是一片险境,迅速通过才是上策。幸运的是,尽管面临敌情,但敌势尚不严峻。前来对新四军实施堵截的国民党军第40师,从潥阳、宜兴方向急速赶来;第79师,则从诸暨方向疾驰而至。新四军完全有机会在他们完成合围之前,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队伍抵达茂林时,项英却下令部队暂停前进。
停下休息吧。
在漫长的行军途中,适时的短暂休憩对于恢复与维持体力至关重要。然而,皖南部队此次在茂林的休整,却并非简单的片刻小憩,而是一次长达一天的彻底休息。从5日下午三点直至6日黄昏,部队方才重新踏上征程。
获悉皖南部队在茂林受阻后,毛泽东与朱德迅速向叶挺、项英发出紧急电报:“鉴于茂林地区不宜久留,待宣城、宁国一带局势清晰,即刻东进,趁敌军部署未定,突破其包围圈,为我方争取有利时机。”
遗憾的是,毛、朱所忧虑的终成现实。茂林长达二十余小时的休息与等待,致使宝贵的时间落入敌手,国民党军的两师得以悠然抵达阻击阵地,顺利占领了阵地,对我方实施了严密的包围。
无人能够阐明为何项英会在与敌人竞速的过程中选择整日休息,此谜团至今尚未有人能够揭晓。
气人?别急,更气人的在后头。
继在星潭的突破口已被成功打开之后,我方却意外地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导致敌人得以重新封锁。
7日凌晨,中路第二纵队及其所辖军部抵达星谭周边的百户坑,随即展开左、中、右三路协同进攻星谭的作战部署。
星潭,作为南线转移的关键节点,乃必经之地。若能攻克星潭,则可趁机突破重围;若未能拿下,则突破之路将遥不可及。因此,星潭之战,势在必得。
然而,原本规划的7日午前对星潭的三路并进计划未能如预期执行,左右两翼均因遭遇敌方顽强阻击,未能按计划抵达,致使原本的三路并进演变为单一路线作战,且在进攻过程中遭遇了更为顽强的抵抗。
如何是好?项英主持召开了军分委的扩大会议,进行研讨与审议。
在会议讨论进行之际,指挥星潭进攻的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来电,恳请增派两个营的支援,以确保星潭的攻克。
叶挺综合掌握的情报,指出敌军防御并非毫无破绽,我军士气旺盛,伤亡亦不严重。若再增派两个营的兵力,攻克星潭当属易事。星潭地处顽军包围圈的外围,虽需再经历数场激烈战斗,并不可避免会有一定牺牲,但牺牲一小部分兵力,以确保大部分部队成功突围,仍有相当把握。基于此,他坚决主张增援。军部作战科长、侦察科长等官员亦赞同军长的见解,急切地请求迅速下达命令,加大对星潭的攻势。
这仅是一项常规的战术举措,依据常规程序,军长理应即刻作出决断,无需召集会议商议,政委亦不会插手干预。然而,在新四军中,军长并无此等权力。叶挺等人的建议再度遭到项英的否决,星潭的增兵计划亦被明令禁止。
星谭前线战事激烈,孤军奋战之际,军分委的会议亦持续进行中。
在当今战机瞬息万变、分秒宝贵的时代背景下,这场会议自午后三点开始,持续至夜幕低垂,不休不止,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下定决心。
夜已深至十点,会议依旧未见终结的迹象,叶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躁,怒容满面地对项英说道:“时间即是胜利,我们绝不能迟疑不决,更不能缺乏决心。我的立场是,即便决心有误,我也将予以遵从。此刻,恳请项副军长做出决断,无论您作出何种决定,我都将全力执行。”
新四军军分委系党的机构,项书记对非党成员叶挺的见解选择不予采纳。会议遂继续展开。
谈及这二纵队的新三团,实乃英勇之至。面对兄弟部队未能如期抵达,且无援军支援的极其不利局面,该团经受了无数艰苦的战斗,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依然在敌军重兵据守、险要坚固的防线中硬是劈开了一道裂口,成功突破敌军前沿阵地,进而攻入了星潭。
然而,正当该团持续拓展战果并向深处推进攻势之际,他们却突然听到了撤退的号角声。
起初,他们难以置信,便要求司号长重新仔细聆听一遍。在再度聆听后,司号长确认无误,告知我们须即刻撤出战场。
他们依旧抱持怀疑,遂派遣通信员与紧随其后的第二梯队取得联系,而那第二梯队却已按照命令开始向后撤退。
在极不情愿的心态中,新三团虽历经血战攻入星潭,最终还是只得遵从命令,撤退而出。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以生命之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竟被舍弃,原本敞开的突围之路再次被无情封闭。
事实上,经过军分会一连串漫长而深入的会议讨论,项英最终作出决策:放弃进攻星潭,并改变原有路线。部队遂决定撤回,转而退守至丕岭西部,沿高岭、太平一线转向黄山,并等待时机,伺机北渡。
号令既出,全军便沿既定行进轨迹,调转方向,踏上了返回的征途。
跋山涉水数日,所行之路竟成徒劳,既已打开的缺口,竟又轻易地让敌人重新封锁。这种异常举动,在干部战士的思想与行动上引发了极大的混乱。
常言道,屋漏偏逢连日雨。正当项英率领部队准备从高岭发起突围之际,临时招募的向导却误将廉岭认作高岭,致使部队误入歧途。这不仅耗费了军力,更挫伤了士气。待部队意识到错误,试图返回高岭时,却发现原本无险可守的高岭已被敌军重兵把守,难以逾越。
再次退回,继续会议。
一番激烈的讨论研究过后,我们最终确定了采取北线策略。此北线,正是叶挺在行动前力主,却因项英的反对而被搁置的路线——即经铜陵、繁昌一线渡江,最终抵达无为的转移路径。
项英曾是历经三年游击战的老将,让人不解的是,他为何直到此刻才作出这样的抉择,对方是否还会如往常般对你保持宽容?
自那场激战以来,时光匆匆,原本防御薄弱的通道,如今已不复往日。江面上,日军舰艇密布,而沿途则被层层顽敌所封锁。战机已逝,良机难再。
路不通,部队再退。
辗转反侧,部队在疲惫与徒劳的旋转中,终究误入绝境,被敌军四面楚歌的包围所困。

四、失败
正当整个部队深陷重围,迫切需要一个坚定的核心人物引领方向之际,项英——一位拥有丰富党龄、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且实际上执掌新四军大权的领导者,一个视皖南部队如同己出、实行家长式管理的领导者,竟然出人意料地犯下了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他抛下部队,仅带少数人擅自行动。
项英在此时此地的举动,宛如一位舰长在海上炮火连天之际,不顾全体舰员的安危,独自驾驶救生艇逃离战场。
延安闻悉项英擅自离队,怒不可遏,遂紧急下令将皖南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全权交予叶挺,并坚定地决心突破重围。悲乎叶挺,在担任军长三年有余之后,方才在这个关键时刻,首次获得了本应早享有的军长全权指挥之权。
遗憾的是,已为时晚矣!太过迟了!弹药耗尽,粮食告罄,士兵们疲惫不堪,敌人密布的包围如同坚固的铁壁,又岂有逆转之机?
最终,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中,仅有千余人得以零星突围,其余大部分壮士不幸陨落。
突围以失败告终。
在中央对事变后续所颁布的《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此次之败……与一般寻常的战斗失利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是否存在内奸的阴谋,尚需进一步调查确认,然而其中诸多细节,确实让人不禁产生疑窦。”
不久后,项英遭其警卫副官所害,中央的疑虑和调查似乎也将就此终止。然而,项英在事件中采取的一系列举动,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不禁要问,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是否出现了异常?若他心智健全,又该如何合理地解释他的行为呢?
十大配资平台app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