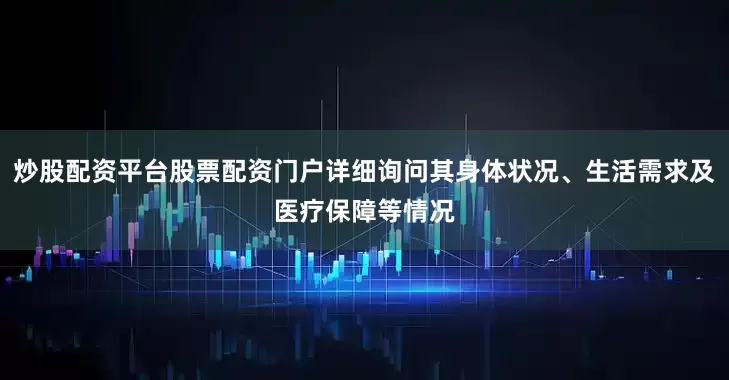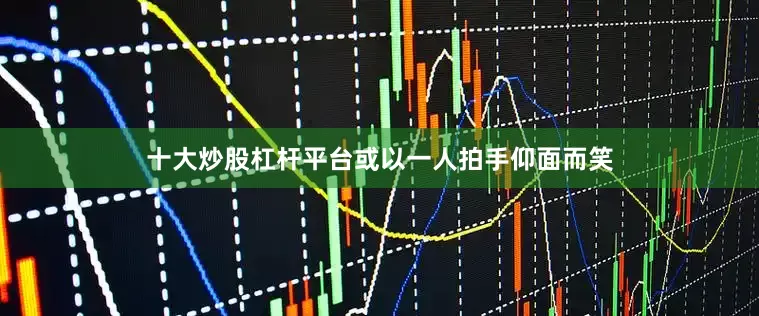
文章来源自凤凰网读书(ifengbook)
作为一名记性不大好的文科生,我读书时最大的困扰就是:这知识它真的不进脑子啊!从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到费曼读书法,我尝试过无数种记忆方法,却因此陷入更大的“记忆力焦虑”——为啥别人不仅看书看得快,还能看完就记住?
没想到,这种焦虑,古代就有了。 “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这种词早就流行了起来,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士人们追求的目标。于是,各种读书方法、记忆方法被发明出来、流传开来。
今天的文章将分享 几种古人的“读书法”,不管什么时代的文科生,为了记住知识点都拼尽了全力啊。
📖本文摘编自《歧路彷徨》,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一目十行”(或“十行俱下”)一词较早的知名典故来自《北齐书·文襄六王传·河南康舒王孝瑜传》:“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十行俱下与覆棋不失一道并用,以十行俱下形容读者的速度,而覆棋不失一道,则是下完棋后仍然可以根据落子先后次序,从第一手覆到最后一手,以此形容其记忆力佳。
展开剩余93%由于行棋有逻辑可循,所以覆棋不失一道虽然不易,但仍非难以企及之事。此后一目十行俱下便独立流行,而专指士人读书速度甚快,直到明清仍常见这类词。
影视剧《啼笑书香》
除了一目十行,另有关于“过目成诵”的记载。
《广韵》对“诵”的解释是“读诵也”,古人读书常会朗读出声,所以应是朗诵、诵读之意,而“过目成诵”则常指其能够记忆内容。
一目十行过目即诵可说是许多士人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会因时代不同而有别,而且跟两个条件有关,一是书籍的数量,一是记诵的用处——主要是为准备科举考试。
这两点都可以在隋唐与两宋之间划出分界。
首先,隋唐以前的书籍流通数量有限,许多后世人手一本的书籍,当时未必能够轻易获得,只有少数人才可能读到全部儒经。
但两宋以后雕版印刷术流行,士人较诸前代更可能接触到各类书籍,尤其是明中期以后,书籍流通更盛,书籍市场亦更蓬勃,加上书籍的价格大幅下降,许多人都可买得起书,于是士人不仅有了通读十三经的条件,甚至也可轻易涉猎史、子、集类的书。
其次,宋以后的士人须借由读书考试以取得功名,记诵是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尤其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是以制艺写作为主,而制艺是儒经的经义之学,理想上士人必须熟习全部儒经,所以对记诵的要求更加明确。
方法一:
欧阳修读书法
明确规定每日记诵内容
欧阳修的读书法虽在宋代提出,但在入明以后更加流行,受到明人的重视。
它要求士人必须记诵全部的儒家经典,所以不仅计算儒经的总字数,而且根据总字数换算出平均每日须记诵的字数,最后更宣称这是让中人或中人以下之士所遵循的标准,亦即这是最低要求,是绝大多数士人都能够做到的程度。
影视剧《儒林外史》
欧阳修的读书法如下:
立身以力学为先,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孝经》《论》《孟》、六经,以字计之:《孝经》一千九百三字,《论语》万有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万四千一百七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诗》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礼记》九万九千一十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为准,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稍钝,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其余触类而长之,虽缕秩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所不至!
欧阳修读书法流传很广,而且被收入元人所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的《欧阳文忠公读书法》条中,俨然成为士人所应追求的典范。
这个读书法所未明言,但又极为明显的意思是:若有人无法做到,就是自甘于闲逸偷惰,所以长辈教导子侄时,也会引用此读书法,如清初姜宸英(1628—1699)与子侄论读书时说:
读书不须务多,但严立课程,勿使作辍,则日累月积,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遗忘。欧阳公言《孝经》《论语》《孟子》《易》《尚书》《诗》《礼》《周礼》《春秋》《左传》,准以中人之资,日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稍钝者,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今计九年可毕,则日读百五十字。
综言之,此读书法对记诵能力立下很清楚的标准,每日几字、应记诵哪几本经典,都有很具体的规定,而且宣称这只是中人之法,亦即对四民之首的士人而言,这应是大多数皆可行的。
过去士人若见人有日诵万言或过目不忘的能力,或会将之视为超凡才能与传说,咏叹赞美而视为不可及。但如今欧阳修读书法所规定的日诵三百字的进度,却让士人无可推诿,避无可避,而不得不面对与承担记诵全部儒经的压力。
方法二:
利玛窦记忆术
一字寄一处
这股风气让不少人十分焦虑,毕竟每个人的记忆力有别,尽管一日三百字,看似是中人亦可达成,但所规定记诵儒经的字数,加总以后达数十万之多,若想维持不忘,洵实不易。
偏偏该读书法规定应记诵的儒经跟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并非是为了炫耀博学而设,所以又让士人很难推诿不理,于是士人不仅必须“六经不可一日去手”,而且还有“夹袋六经”(类似巾箱本)的发明,以便士人在行住坐卧间皆可背诵。
影视剧《儒林外史》
这种不安或焦虑,不仅限于没有功名的士人而已,即连举人、进士中亦有人为此而倍感压力。
如明末徐芳,他是进士出身,但连他也为记忆力所困扰。所以徐芳试图发展一种记忆术,利用摘要的方式以帮助记忆,但仍可想见他对记忆力的焦虑与不安。
徐芳说:
故尝以为古人之学,博闻之外,必资强识。而卷籍委积,非有异慧绝世,终不能兼综无漏。莫若即其辞事之该切宏钜者,编缀成书,使口可诵而帙易书,于目无繁营,而胸有坚据,庶乎刬芜塘滥,以归精约之道也。
徐芳的记忆术,让人联想到一度流行于晚明的利玛窦的西洋记忆术。
利玛窦在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与当时士人有很频繁的往来,而他注意到中国士人对记忆的执着与焦虑,在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中,便指出利玛窦利用记忆术吸引士人的目光,如利玛窦谈到石星之子,他在科举考试落榜后,身心都处在接近崩溃的状态,利玛窦便利用他对及第的渴望而传授其记忆术。
利玛窦对此记忆术很有把握,他很肯定得授此记忆术的学生将有十分惊人的成效,他说:
凡记法既熟,任其顺逆探取,皆能熟诵。然后,精练敏易,久存不忘。
利玛窦以文言文写作《西国记法》,让我们可以得窥其记忆术的大致内容。
利玛窦在此书指出,必须把须记忆的事物化为实在的物件,放置在想象的处所中,而且针对中文的文字特点,设计出多种把中文文字转为图像的方法。
他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为例,记忆方法是:
以俊秀学童立观书册为“学”字,以武士倒提镋爬象“而”字。以日照寺前,一人望之,象“时”字,或以姓“时”、名“时”之人。以日生两翼,一人骇观,象“习”字,或以姓“习”、名“习”之人。以一人持尺许之木,削断其头,象“不”字。以一人肩横一戈,腰悬两锤,象“”字;“”,篆文,即“亦”字也。以傅说筑岩,取“说”字,或以一人拍手仰面而笑,亦象“说”字。以一胡人胡服而居,假借“乎”字。以上九字,逐字立象,循其次第,置之九处,此盖一字寄一处之例也。
简言之,就是用形象的方式记忆每一个字,然后每个字在记忆宫殿中各有位置,也就是“一字寄一处”的意思。
方法三:
服药开悟
以“日诵万言”为目标的药方
除了徐芳及利玛窦的记忆术以外,医书也相当程度反映了人们对记诵能力的追求。前述“日诵万言”只有上才者才能做到,两宋以来的一些医书便以“日诵万言”为目标而开处方。
如流行甚广的铁瓮先生琼玉膏便跟此有关,此药方最早见于南宋洪遵(1120—1174)的《洪氏集验方》,用药是人参、生地黄、白茯苓:
此膏填精补髓,肠化为筋,万神具足,五脏盈溢,髓实血满,发白变黑,返老还童,行如奔马。日进数食,或终日不食亦不饥。关通强记,日诵万言,神识高迈,夜无梦想。
此处主述对修炼成地仙的益处,日诵万言只是成效之一。
影视剧《啼笑书香》
至于北宋张君房所编的《云笈七签》中的“开心益智方”与“安神强记方”,而服食其方的效果,虽亦与成仙有关,但也有增强记忆的效果,前者的药方是胤粉、菖蒲、远志、人参、龟甲、署预、龙骨——
服得百日,心神开悟;二百日,耳目聪明;三百日,问一知十;满三年,夜视有光,日诵万言,一览无忘,长生久视,状若神明。
后者的药方是胤丹、防风、远志、天门冬、菖蒲、人参、茯苓及通草——
服得三百日,旧日之事,皆总记之;六百日,平生习学者,悉记俨然;九百日,诵万言,终身不忘。
南宋张杲的《医说》所引的《健忘诗》,同样以日诵万言为目标:
健忘诗云:桂远人三四,天菖地亦同,茯苓加一倍,日诵万言通。
桂远人即官桂、远志、人参;天菖地即巴戟天、石菖蒲、地骨皮。以上不断出现的菖蒲应即石菖蒲,与远志同样都有安神益智、治健忘的功效。
方法四:
朱熹读书法
书宜少看,应极熟
前文谈到欧阳修读书法的流行,以及科举考试的制度化,使得记诵儒经一事备受重视,但同时代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也不会只有单一标准。
当人们一味追求记诵儒经时,宋明两代的程朱学者与心学家皆指出另一条路、另一种选择,这个选择不是反对记诵,也不是要求士人不必记诵,而是对记诵儒经提出另一种见解与立场。
朱熹多次回答门人弟子有关记诵的问题,而这些对话多被收录在《朱子读书法》中。在此书中,朱熹否定秦汉以来重视记诵的读书法,他说:
自秦汉以来,士之所求乎书者,类以记诵、剽掠为功,而不及乎穷理修身之要。
两宋理学本有质疑秦汉以来学术的倾向,朱熹甚至批评秦汉以来的读书法是以记诵剽掠为功,对此我们固然不必同意其评语,但朱熹把秦汉与两宋理学的读书法截然划开,去彼取此的立场则是确定的。
不过,朱熹并未否定记诵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记诵是为了理解义理,所以引张载的话说:
横渠(按:张载)云:书须成诵,精神都是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
又说:
书只是熟读,常常记在心头始得。
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
主张“书须成诵”,理由是:必须成诵,才能够时时反思回想。所以不仅不特别强调记诵能力,而且更建议应“宽着期限,紧着课程”,意即日日皆须用功,但可少读慢读,即使一日仅读一两百字亦无妨,他说:
书宜少看,要极熟。小儿读书记得,而大人多记不得者,只为小儿心专一。日授一百字,则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则只是二百字;……宽着期限,紧着课程。
以及必须多诵遍数,他说:
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读书法且先读数十过,已得文义四五分,然后看解,又得二三分,又却读正文,又得一二分。
这两点正与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要求相反,所以当有人为资质鲁钝,记忆力不佳而苦恼,朱熹便开导说:
时举云:某缘资质鲁钝,全记不起。先生曰:只是贪多,故记不得。福州陈晋之极鲁钝,读书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后能熟,积累读去,后来却应贤良。要之,人只是不会耐苦耳。
这段对话很有趣,因为类似的对话大概很难发生在前文所举的那些记忆力极佳的人身边,他们自身既不会有此忧虑,而且在炫耀与标榜记忆力的风气下,“资质鲁钝”的人很容易被排挤到边缘,而难有发言权。
但这些人却愿意向朱熹诉苦,而朱熹也宽慰之,鼓励他们不必好高骛远,只需从五十字做起,即使读诵三百遍之多才能记下亦不妨。
方法五:
读书分年日程
宽着期限,紧着课程
朱熹“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原则,以及强调遍数、一点点积累到极熟的做法,影响所及而有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
据其读书法,依序有读经日程、看史日程、看文日程、作文日程。经书须记诵,史籍须熟读,看文、作文则直接跟科举写作有关。
此书规定:
日止读一书,自幼至长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语。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仿此。
至于读书的工夫,则是秉承朱熹说书须极熟的主张,所以每天除了新功课以外,还必须把前几天所读的再复习过,具体方式即分段看读百遍,背诵百遍,然后再通篇背读二三十遍。
影视剧《啼笑书香》
如其所言:
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决无不熟之理。
也因此,从八岁入学始,须花六到七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包括《小学》《四书》及几部经书的正文读熟。
但有必要注意的是,此处规定每日所须记诵的字数,虽以一二百字为基础,但以能够达到近千字为佳,等于是“日诵千言”,这也显示朱熹的读书法虽尽量不突出科考的压力,但到了《读书分年日程》却已无法满足于每日仅读一二百字而已。
《读书分年日程》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末仍有实践者。
方法六:
王守仁读书法
不能有强记之心
明中期阳明心学兴起,在心性学说及对儒经的解释虽与程朱学立异,但批评记诵的态度则是一致的,而且走得更远。
若是跟程朱学必须穷尽万事万物之理,等待“一旦豁然贯通”相比,王守仁主张必须提挈良知,而且良知超然于见闻之上。
朱、王的学术之辨有极精细而复杂的部分,程朱学并未把心性与见闻混淆为一,但我们若是把阳明心学与同时代的程朱学末流相较,阳明心学确实更侧重在心性良知的这一面。
对于士人所关心的举业文字,王守仁也用良知来说:
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不能有强记之心,不能有欲速之心,不能有夸多斗靡之心,凡此几种心,皆与一目十行、日诵万言的趋向相近相通,而必须用良知克去。
《训蒙大意》则可视为王守仁的读书法,他说: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
大旨是读书贵精熟,以及对能读二百字者只授予一百字,而且必须䌷绎反复字句,直到领悟其字义为止。这虽是教导生童之法,仍可反映王守仁的主张。
跟前引朱熹谈读书法相较,两人都求精熟而不求多读,也都强调专心一志、反复诵读。我们甚至可以说,尽管朱、王二人对心性义理的见解有别,但王守仁却以良知学引导人们重新回到朱熹的读书法的原则及精神。
本文摘编自
《歧路彷徨》
副标题: 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
作者: 张艺曦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出版年: 2025-4-1
发布于:北京市十大配资平台app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